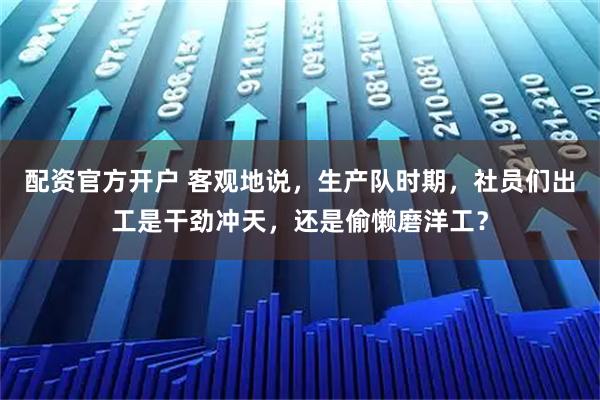
1970年代的某个清晨,在河北一处生产队的田地旁配资官方开户,伴随着鸡鸣声,队员们开始了一天的劳动。大家手里拿着锄头,面带疲惫的神情,缓慢地走向田埂。随着一声哨响,队员们纷纷分开,开始干活。
队长老刘看到这一幕,不禁皱起了眉头,他心想:“这些人看起来真的没有干劲!”但他也明白,凭着那点工分,大家没什么动力去拼命工作。那么,是这些社员懒惰,还是因为体制让他们只是“走个过场”呢?
生产队时期,工分制几乎家喻户晓。很多人一提到工分制,就认为这是激励大家劳动的动力。毕竟,每天干活儿都能积攒工分,年底不仅可以换钱,还能换粮食。可事实是,工分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起。
展开剩余82%工分制的出现让队里分出了“老把式”和“懒把式”。那些干得勤快的,和偷懒的社员一眼就能分辨出来。可是,工分制的规则是按人数来分,做得多和做得少的分数差距并不大。这让那些埋头苦干的社员,比如老李头、王大婶,开始抱怨:“无论多么卖力,也不会比混日子的人拿得少,这算什么激励?”
这让生产队内的气氛变得两极分化。一些人天天琢磨如何混水摸鱼,尽量少干活;而另一些人则尽力干活,却始终积累不到足够的工分。那些拼命工作的社员本来希望能赚点工分,结果发现辛辛苦苦得来的工分换不到多少东西。有些人甚至自嘲:“一天到晚干活,胳膊酸腿儿疼,最后拿着工分回家煮‘寡汤’,真是人也难,汤也寡。”
在这种环境下,社员们的干劲儿逐渐消耗殆尽。虽然有一些生产队的管理较为严格,队长和生产小组长时刻盯着社员,稍微有懒散的迹象,立马让他们“补补劲儿”。但也有些聪明的社员,发现工分制不过是“按头数吃饭”,干得多干得少最终差距不大,于是他们干脆轻松地背上锄头,悠闲地在田间晃悠。
结果,很多生产队的工作状态就成了“出工不出力”。虽然大家都到地里了,但锄头一拿起,力气却似乎没有全用上。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蔓延开来,社员们的劳动热情逐渐被削弱。
不过,也有些生产队严格管理,采取了轮岗制,指定专门的“监督员”来检查是否有偷懒现象。一旦有人磨洋工,立马被点名批评。但问题是,大家在一起工作久了,难免产生人情关系。许多监督员对邻居不好意思指责,结果对偷懒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在某些队伍中,甚至干脆把“轮岗”当成了摆设,大家心知肚明:“今天你管我,明天我管你”,互相照顾,偷懒的事大家心照不宣。这种人情化的管理方式使得社员们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,许多生产队都成了“偷懒大军”。
然而,1978年,小岗村实施的包产到户改革为这一切带来了变化。包产到户后,地分到了个人头上,每家每户自己负责,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支配。这种新方式直接激发了社员们的干劲,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。大家看到干得多挣得多的好处,纷纷投入更多的精力。
小岗村的成功让全国的生产队都看到了希望,其他地方的生产队也开始纷纷效仿。因为大家意识到,真正的激励机制并不是让所有人按头数分工,而是要让社员们通过努力获得实际的回报。生产责任制的推广使得社员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,社会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。
回过头来看,在没有激励的生产队里,许多社员对工分制并不感兴趣,甚至有些人调侃:“一锄头下去能挣几毛钱?这锄头挥下去,累得我都快撑不住了。”没有了利益驱动,干活成了纯粹的“形式”,没有人真正用心去做。
然而,小岗村的成功却证明了一个道理:适当的激励和自主权,才是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关键。生产队时期的干劲与偷懒的现象,实际上取决于当时的制度设计和社员的心态。当激励机制到位时,人们的劳动热情自然被激发出来,大家也不再只是“走个过场”。
发布于:天津市博星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